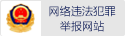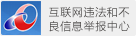京ICP证150520号 | 京ICP备15016857号-2 | 新出发京零字第朝230045号 | 联网备案号11010502038006 | 京网文(2015)0522-202号 | 京公网安备11010502038006号 | 软著登字第10302139号
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许可证:(京)字第13450号 |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A2.B1.B2-20230296 | 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邮箱:kefu@haolvshi.com.cn
Copyright©2015-2025 好律师 haolvshi.com.cn版权所有